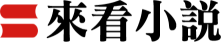秦風和張明深說得很清楚。
他要再去看一看,上次是佟言和他告別,這次他跟她告別。
他說得天花亂墜,無比誠懇,張明深毫不留情的揭穿他,“你說的話你自己信嗎?”
“我認真的,我不放心,周南川就是個混子,我怕他對她不好。”
“對她不好怎麼了,佟家都沒去管的事,你能管?”
“我不能不管。”
“你就是想讓她跟你私奔。”
無論秦風說得多麼誠懇,張明深相信自己的直覺,秦風承認,這種想法不道德,不負責,但他就是想最後瘋一回。
他三十多了,頭一回爲了一個女人這樣。
秦家,佟家,他不想管了。
“你先想明白這樣做會帶來什麼後果。”
秦風沉默了幾秒鐘,啪的一聲掛了電話,將手機關機了。
他得找到他的女人,帶着她離開這個鬼地方,不再讓她水深火熱,那才是他作爲一個男人應該做的。
下午周南川帶着佟言買了幾條孕婦穿的褲子,送她回家的路上接到了電話,帶着客戶去園子裡逛逛。
佟言大肚子沒辦法陪同,在鐵皮屋裡休息,一睡一下午就過去了。
接近傍晚,她緩緩的睜開眼睛,周南川買了點吃的回來。
外面很冷,下了雪,佟言在牀上睡得很暖,不想起來,周南川將她拎起來餵了點吃的。
“你媽不讓我在牀上吃東西,說會把被子弄髒。”
“吃,弄髒了我來洗。”
佟言側着抱着男人的腰,小臉也貼在他腰上,剛從外面回來的男人,身上有點冷,“周南川,你上來躺會兒吧。”
“你先吃飯,餓着肚子我心裡不安。”
佟言起身端起盒子吃了幾口,周南川給她把外套蓋上。
“我吃飽了。”
“這麼點?”
男人將她吃剩的東西吃了,又開了另外一盒填飽了肚子,佟言吃飽了就犯困,又要睡着了。
周南川收拾外賣盒子放在鐵皮屋門口,手機忽然響了。
打電話的是園子裡的幫過。
“川哥,我剛才看到一個人進園子了。”
“什麼?”
“一個男的,穿着黑色的風衣,縣裡年前不是鬧兇殺嗎?我看他眼生想問清楚,又怕是你認識的人,你出來看看吧,要不認識你也有個準備。”
“什麼時候看到的?”
“剛才,我和我老公從那邊路過,尋思跟你說一聲。”
外面已經黑了,園子這麼大,不熟的人從外面進來要走好一陣,他拿了根棍子想去找人,大掌握了握,很快又鬆開了。
他自嘲的笑了,回頭看了一眼屋門口。
佟言要睡着了,被周南川開門的聲音吵醒,她伸了懶腰。
“是要回家了嗎?”
“今晚就在這睡。”
男人說着便脫衣服上牀,佟言瞬間清醒,“什麼,可……”
“這邊什麼都有。”
還沒等她說完,周南川捂着她的脣,一隻手撐在牀上,另一隻手很快開始不老實,佟言微微蹙眉,好不容易才將他推開了一點。
男人的眼神充滿危險,她心亂如麻,大腦一片空白,“周南川,你幹什麼呀?”
她捂着肚子往後一縮,“懷孕了,不可以的。”
周南川沒再親她,灼人的眼神盯着她看,捏了捏她的臉,“言言,過了三個月後可以適當的做一做,別那麼傳統。”
“你騙人。”
“我不騙人,真的,我忍得很難受的。”他抓着她的手,在他臉上摩挲着。
“我是你男人,我們之間什麼都可以。”
佟言怕疼,但周南川此刻的樣子挺可憐的,好多時候她不願意,他也妥協了,一個人在廁所裡面,那麼冷。
佟言不知道說什麼好,安撫的親了親他,但他回應的並不是溫柔的吻,她感覺得到,他很渴望。
好幾分鐘,佟言輕輕地將他推開,“真的很難受嗎?”
“嗯,好難受。”
“可我怕疼。”
“我輕點,慢點,行嗎?”她沒說話,算是默認了,周南川低頭吻着她的脣,溫柔至極,一點點的與她坦誠。
秦風找了好久才找到這麼一間鐵皮屋,蹙着眉頭看了一眼上去的板梯,擡腳正要往上,聽到了女人的聲音。
有那麼一刻他大腦一片空白,不信邪,想再次靠近點,裡面的聲音再次穿過來了。
“你輕點……”
“好緊啊,言言。”
秦風拳頭緊握,眼神頓時黯淡了,他想走到門口,卻發現自己沒有那個勇氣。
動靜越來越大,他有些麻木了,走到了門口。
“喜歡嗎,是不是不疼了,嗯?”
“說話啊言言,喜歡嗎?”
“嗯……”
聽到最後的時候,秦風跑了。
佟言聽到了外面的動靜,緊緊的抱着周南川,小聲問,“外面有人?”
“沒有,今天風大,下了雪。”
今天風大,下了雪,樹梢的雪沒有化,秦風走到園子門口又折了回去。
寒風吹在身上,吹在心裡,他蹲在聽不到動靜的地方點了煙,一根又一根,蹲得腳麻,抱着膝蓋也沒辦法暖和一點。
不是她的錯,是他沒在她需要的時候陪着她。
屋內,佟言躺在被子裡睡着了。
懷孕的緣故周南川不敢折騰她很久,可她體力確實不行,在他完事兒後累得睡着了。
男人穿上了衣服,摸了一根煙緩緩往外面走,神清氣爽。
一記拳頭就這麼過來了。
他有準備,但沒反擊,指尖夾着煙,無比淡定的看了他一眼。
秦風渾身冰冷,幾乎有些站不穩,一個踉蹌揪着他的衣領,咬牙切齒,聲音顫抖,“周南川,你強迫她是不是?”
“你在說什麼?”
他喉頭一緊,“剛才,你強迫她,我問你是不是?”
“我們是夫妻,什麼強迫?”
周南川將他甩開,意味深長盯着他看了幾秒,“你還有偷聽男女親熱的癖好?”
秦風徹底沒了話,周南川朝着他走了幾步,看了一眼他的腿,“你這次過來,是想讓我再斷你一條腿?”
秦風盯着他,周南川要笑不笑的,“還不滾?”
秦風頭皮發麻,半條命都沒了,像極了落魄的流浪漢。
周南川抽了一口煙,沒對他動手。
過了好一陣,他才開口,“周南川,你對她好點。”
沒等周南川說話,他從兜里拿了個手鍊,“幫我給她。”
說完後便走了。
周南川在外面抽完了煙,接到鄧紅梅的電話,“媽。”
“還不回來啊,我跟你爸等你們吃飯呢!”
“你們吃吧,我們晚上在園子裡住。”
“什麼?年都沒過完怎麼又到園子裡住嗎,不是說好了回家的嗎?”
他當時沒了主意,也沒顧得上提前發信息回去,他有點不耐煩,“我累了,就在這睡,你們吃你們的,明天回來。”
說完直接掛了電話,繼續看這條手鍊。
跟普通的銀質手鍊沒有區別,但仔細看可以看到上面的字樣,很精緻,也很小。
有塊白色的小圓餅,上面刻了字,很土:秦風和阿言永遠在一起。
小圓餅很小,字也很小,擠得要命。
他心想,真夠矯情的。
如果他沒記錯,佟言也有一隻這樣的手鍊,剛來的時候她戴過,但他一直以爲只是裝飾品,從沒仔細觀察過。
去他媽的裝飾品。
他順手扔進了林子裡,又點了一根煙。
“周南川!”
他一個激靈,轉頭回到了屋裡。
“你在外面幹什麼?”
“抽煙。”
佟言見他臉色不太好,剛從被窩裡出來的手去捧他冰冷的臉,她一臉認真,“你臉上怎麼了?”
周南川毫無防備,摸了摸剛才被揍的那邊,乾笑道,“剛才不小心摔了。”
“怎麼摔的。”
“爽得腿軟。”
佟言紅了臉,爽得腿軟?怎麼什麼都說得出口。
“你不要臉!”
周南川抱着她,“言言,以後什麼事都跟我說行不行?”
“先別說這個了,快上來。”
“還沒洗腳。”
“你先上來暖和點,你手好冷呀。”
“心疼了?”
“我怕你感冒了傳給我,我又不能吃藥。”
兩人躺在牀上,佟言躺在他懷裡,頭髮絲挨在他下巴上,痒痒的,“周南川,上次睡覺的時候我發現你腳指甲好長啊,你平時不剪的嗎?”
“沒時間,可能忘了。”
佟言從牀頭的位置摸出了指甲刀,“我本來打算等你睡着了給你剪的,但你睡覺喜歡亂動,踢到我就麻煩了。”
周南川在她額前親了一下,“言言,我們明天去市里看房子好不好?”
“這麼着急?”
“買了房你想裝修成什麼樣都聽你的,我們住一間主臥,給你弄一個畫室,再弄一個書房,給孩子一個嬰兒房,他出生以後在市里念書,我們早上到園子裡順便送他上學,早點下班去接他。”
佟言語氣懶懶的,“是不是有點遠了?”
這話讓他莫名緊張,“怎麼這麼說?”
“一個畫室一個書房,你爸媽來了住哪裡,客人來了怎麼辦?而且孩子還沒出生呢。”
“那我們買個更大的,買個別墅?”
周南川手裡的錢,買別墅是綽綽有餘,但園子每年要投進去不少,明年的情況還不知道怎樣,佟言不想他那麼累。
“我不住別墅,不喜歡,房子大有什麼用?”
“我不想委屈你。”
“我才不委屈,你買個比雄慶大一點房的就可以,氣死他們家。”佟言說這話一臉傲嬌。
周南川忍不住去捏她的臉,“你跟誰學的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