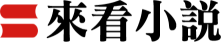“如今還想坐享齊人之福,怕是不行了。”
肖海舉起了手裡的杯盞,嗤笑了一聲看向段承軒,旁的桐舟則是微微皺眉,似是有些不滿,只將肖海手裡的杯盞給奪了過來:“一命換一命,倒是不如不換。”
肖海眼睛睜大了些,倒也沒從桐舟的手裡將杯盞搶過來。
唯有段承軒坐在主位之上,一杯又一杯的飲了酒水,看着肖海和桐舟。
倒是從未想過,他也會因爲感情之事來跟兄弟商討。
聊了許久倒是也沒有個結果,反而是他喝的半醉,只向肖海道了別,這便來到了鳳鳴苑中,他倒是已經習慣了和顧茗煙同牀共枕的日子。
躺倒在牀褥,眼前的人兒有些模糊,他甚至都忘記了那人還身懷有孕。
只記得顧茗煙今夜難得熱情。
日上山頭,破曉天光。
窗外傳來幾聲鳥雀啼鳴,段承軒便霍然睜開了眼,眼前的房間倒是鳳鳴苑的,惹得他忍不住的一陣頭暈目眩,只怪昨日桐舟帶來的酒太烈了些,腰上卻搭上了輕軟的手臂。
“醒了?”段承軒輕聲開口。
和顧茗煙同睡之時,她總是醒得早,睡覺也淺的很,段承軒每每一動,顧茗煙便總是醒來,今日卻有些意外。
她是睡得迷糊了,才如此熱情?
可當他抓住了那手腕,卻猛地從牀上坐了起來,將方才的枕邊人給摁在了牀榻之上。
“王爺!”顧子衿驚呼了一聲,感覺到自己的手都要被折斷了。
門口的阿蘭成山聞訊沖了進來,阿蘭一看見顧子衿便馬上沖了過來跪在了地上:“王爺還請手下留情,小姐到底還是您的的妾室呀。”
妾室二字倒是讓段承軒清醒了過來。
在看清了那人只着一身裡衣的情況之下,段承軒便直接鬆了手,從牀榻上爬了起來,只覺得牀榻之上的那一抹紅如此刺眼。
成山也睜大了眼睛看着房中的一切,忍不住的看了一眼院外的匾額,只趕緊跪了下來:“屬下也並不知道爲何二夫人會在此地!”
段承軒只揉了揉額角:“去領三十杖!讓鬼魅過來日夜看着王妃的行蹤,若是再出現此事,決不輕饒!”
“王爺……”顧子衿只拉扯着被褥輕輕的喚了一聲,眼裡盈滿了淚水:“昨日我只是見這鳳鳴苑蕭條,而姐姐懷有子嗣,才同姐姐換的。”
一個女子都如此這般的解釋,段承軒倒是對她沒有半分的責怪,反而是沉下一張臉來:“王妃在何處?”
“應當是在妾身的清風苑裡。”顧子衿的眼淚總算落了下來。
段承軒本就不是什麼憐香惜玉之人,見到顧子衿這般做作的模樣,當即就冷下臉來,將人從牀上拖拽下來,只嚇得一旁的阿蘭趕緊將顧子衿給護在懷中,一言不敢發。
“哭什麼哭,日後你要是再做些小手段,莫怪本王不客氣!”段承軒只從成山手裡接過了外衣,匆匆穿上便向外走去。
顧子衿被嚇得不輕,方才被段承軒拉扯過的地方如同撕裂般的疼痛,眼淚也跟着落了下來,啪嗒啪嗒的落了一地。
阿蘭只趕緊握住顧子衿的手,忍不住的說道:“小姐莫慌,方才成山也特意提點了您是二夫人,只要一切都做的好好的,定然不會出問題的。”
“若是王爺知道那牀榻上的血……”一想到這裡,顧子衿就忍不住的打了哆嗦,只將自己的指尖翻轉過來,那裡正有一個小小的血痕。
阿蘭趕緊將其捂住:“昨日之事,小姐定然不能同其他人說。”
“阿蘭,你究竟是讓我做些什麼?”顧子衿不甘的咬了咬下脣,滿手冰涼,一想到昨夜所發生的事情,竟然是驚出一身冷汗。
今早這次,並非是第一次被段承軒從牀榻上給扔下來。
昨夜,她可是好不容易才能舒舒服服的躺在段承軒的身邊,竟然是什麼事情都沒做。
“顧夫人曾說,您並非正妃,若想要在這靖王府中立足,定然要鋌而走險。”阿蘭只握着她的手,嘴角帶了笑:“今日這一晚,卻是夠了。”
……
而此時的清風苑中。
顧茗煙懷裡還捧着碗熱湯麵,正愁於院子裡的丫鬟沒送來筷子,自己又看不清,偏偏還心神不寧的讓青黛去濟世堂了,如今面對這熱湯麵,除了能品上幾口湯水,似乎並無其他用處,還饞她呢。
正無奈着尋思,眼前那些光亮卻突然被遮掩起來。
“是拿了筷子來嗎?”顧茗煙呆呆的擡起頭來,再捕捉到眼前人影的輪廓時微微愣神:“段承軒?”
“你倒是認得出來!”段承軒看着她捧着熱湯麵坐在這石凳之上,倒是收斂了脾氣沒敢動手,只橫了身邊的成山一眼,後者便趕緊偷摸着吩咐人去將湯勺和筷子拿過來。
段承軒徑直的坐了下來,將她捧着的熱湯麵給放到桌上:“昨日……”
“反正我也伺候不了您,而且您都讓子衿入了府,我倒是覺得並無不可。”
“原來你可以如此輕易的將本王讓給她人!”
段承軒猛地一拍桌案,清風苑所有的人都紛紛跪在地上,顧茗煙也被嚇了一跳。
可等到反應過這句話的意思之時,顧茗煙卻又只能微微張着嘴,說不出一個字節來。
段承軒這般的意思……
“本王倒是忘記了你是個鐵石心腸的女人。”段承軒突然話鋒一轉,言語裡帶了嘲諷的笑意。
桌案上的熱湯麵也灑了一地,碗碟碎片都落在了顧茗煙的腳邊。
顧茗煙方被熱湯麵焐熱的指尖頓時冰涼起來,只死死的攥緊了衣角,緊了幾次,一直等到段承軒的步伐到了院口處,她才鬆了手,輕聲開了口:“王爺已然看清了,煙兒不過是個鐵石心腸的女子而已。”
段承軒停留在門邊,沉默良久。
“本王最厭的,便是你這般狠心女子。”
話音落,秋風輕揚,耳邊只剩下細碎聲響。
顧茗煙只是撩了耳邊的碎發,泛白的指尖扣住了胸口前的衣服,鼻尖發酸,輕聲道:“那你何必過來刺痛我的心呢。”